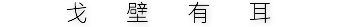这段日子,每天早晨的速溶咖啡是为了能喝到北京五月份的豆汁儿;每天爬三楼的考研自习室是为了能在腊月里登香山看日出;在网上买以15年政治大纲解析还要读三遍,是为了能在美术馆东街的通宵三联书店读网上买不到的三联书。还有七十天,第二个七十天。秋天,又是一个秋天。季节交替的时候最适合去后海伤春悲秋吧?嗯,还有史铁生的地坛。
陋居
昨晚第一次在我租住的地方和老妈视频。“我租住的地方”,讲起来是有些别扭,我就是矫情地觉得这地儿还不足以叫“家”,我也没法顺其自然地说“我每天几点回家”或者“我到家了”这样的话,因为我只在这儿租住四个多月啊,满打满算五个月,初试一考完,我就回家了,会真正的家,离开青岛,可能不会再来了。我也只是晚上和中午在这儿睡个觉,洗澡洗衣,偶尔在这儿吃个饭,所以这里充其量是个宿舍吧。
这里也可以叫“陋居”。1300块一个月的高层住宅也没资格当陋居,可昨晚视频时,我给我妈展示完我的房间后,她就觉得这里是陋居了。你看,我的房间的确很小,床也小,没有衣橱。我用的是上个租客留下的建议的布制衣物收纳橱,刚搬来那天我闻见这橱子散发着浓烈的狐臭味,就拆了支架,把外面那层布扔进洗衣机里搅了搅,后来发现那狐臭味就是这布料本身的味道。我的房间是没有窗帘的,白天房间透亮,像同开五盏日光灯,午睡就比较困难了;晚上房间就太通透,对面那栋楼密密麻麻的灯火让我紧张,万一有个偷窥狂隔楼观我怎么办。因此在搬来的第一周,我就去附近的市场买了一块床单当作窗帘,宜家风,25块。窗户没有窗帘杆,只有左右各一枚钉子,我就用晾衣夹夹住床单两边,刚好可以挂在两边的钉子上。早晨起床,伸手用力一拽,窗帘就“哗”地铺天盖地了,也是方便,但挂上去就比较麻烦,每次都需要爬上爬下。
只要有我在的地方,我能填满一切空档。我这不大的房间已经被我搞的满满当当。没有床头柜,我就用行李箱当床头柜;没有挂衣架,我就支起相机三脚架当挂衣架;没有书架,我就索性在墙根上把书列起来。我欣然接受这样的简朴,也享受这样的简朴,因为我终归要搬走,留下并带着胜利的喜悦。
New Life
大家都开始了新生活。
建建同学在上海的新生活开始了。前阵子在群里告诉我和方佳,说他这几天日子的日子过的很棒,还告诉我“上海的街逛不完,北京也是一样”,以此来激励二战北京的我和方佳。他还发来一条短信,让大家惠存他在上海的新手机号码。在我看来,换号是新生活开始的直接标志,那么,他在青岛的号码应该是作废了。
付博打来电话,问候近况,我惊喜地听出他说话有了京味儿,不浓郁,听的出来是无意染上的。我也用京片儿调侃他,“哟,这一嘴儿京味儿,看这哥儿混不错啊!”他到北京后打算再缓冲几天,十一前去家里给他找的单位报到。
杨任珂在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工作,是候机楼贵宾区安检员。我们总调侃她,要是碰见个明星或是中央领导可以多摸几下。
前阵子还有一好玩儿的事儿。我正在家里抠脚丫,来一电话,是一陌生号码。电话里是一业务娴熟、声线娇好的京味儿女声,是新东方的课程顾问。她很专业,很会聊,她问,我答,聊学习,聊生活,聊未来打算,我也就很耐心地聊下去没有推脱。聊了十分钟,我正着急她怎么还不向我推销课程,她就问我,“先生,我这边想留您资料,您贵姓?”我答姓张,“那您方便告诉我您的全名吗?”我答张戈耳,“您这名字挺好听的,真特别!”我这边真是害羞了,使劲答“没有没有没有”。
“那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新东方课程顾问,我的名字叫$#^&@!”
最后她的名字被淹没在了她刺耳的狂笑声中。我楞了一下,用了三秒的时间反应过来:这他妈是阎旎!阎狒狒!我和她一起大笑不止。因为有段日子没有联系了,以这样的方式突然出现令我实在意外。阎旎是和我认识十年的朋友,期间还因为种种原因,中断联系了近五年。她和退休的父母迁去了北京,租住在二环一小二楼。现任职于某银行培训课程电话销售,还没转正。刚换了北京的号码,就得瑟地想用新号码整人,乔扮过光大银行和新东方,我就是受害者之一。
大家在不同的轨道上各自忙碌着,想想也是挺有意思的。我也开始了我的新生活,虽然还忙碌着学习,而且还是把去年的东西再复习一遍,可仍然有新的未知数和挑战,刺激和紧张程度也不输他们呀。
preview
房东先生
经过我的不懈折腾,我终于能够在自己的本科学校复习了。我和一同系同专业的研友在学校附近合租了一套房子。他考法律硕士,我考翻译硕士;我英语口语好,他英语语法好,学习上也倒能互补。这是我第一次自己租房住。从找房、看房,到签订合同、搬家入住,都是我一个人来完成。一切还算顺利,房东先生人不错,中介也不是很黑。签合同现场,中介的老板出面,和那位房东一起,在我面前是长辈的架势,他们的年龄也与我父亲相仿,所以对我也颇为照顾。
房子是两室两厅,12楼,家具电器齐全,简单装修——也可以等于是没有装修。皆是白墙,但却铺了很好的红木地板。房东在房屋交接的时候拍着我的肩语重心长道:小伙砸,这房子里的家具电器你随便造,就着木地板你可得给我看好了,你看我今儿早上还特地来一躺给地板上了蜡。好说,好说,大不了以后光脚丫子踩就是了。
第一次去看房的时候,只有暂住在这里的房东太太和她儿子在。我们进了房门,房东儿子下了床,指着我、室友和中介经纪人,问房东太太:这三个人是谁呀?房东太太怎么回答的我记不得了,但是他儿子的特殊行为表现,让我和室友下意识别过头去故意没有注意他。后来再次遇见他们,是在房门口,房东儿子躲在电梯间里不出来,房东太太用青岛话大声唤,还是不出来,最后是被她牵着出来的,表情呆呆地看着地板,一路上都是房东和他太太轮流领着他走。从中介老板和房东先生的聊天中,我了解道到他儿子跟我差不多大。
房东先生看上去是个中产,谈吐有涵养,房东太太也很有气质。他们的儿子有智力上的缺陷,可能他们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了吧。室友说,天下没有完美的人。我不好奇他的儿子智力哪方面有问题,但我好奇的是儿子智力上的缺陷是否是房东夫妇内心一块暴露在外的伤疤。他们一家三口走在路上,一个陌生人好奇的眼光也许随时都会刺痛他们。
反正我就是一个害怕把自己的致命缺陷暴露在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