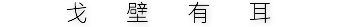年是过完了。对于到目前还一直有寒假可以过的我来说,过了正月十五才算把年过完。
小时候过年是享受,因为什么都不用操心啊,有花炮可以放,有宋丹丹高秀敏的小品可以看,有压岁钱可以毫无顾虑地拿,虽然有寒假作业困扰,但过年仍然是一年里最值得期盼的日子了。爷爷家院子中间有一片不大的菜地,冬天里面堆满了雪。每个大年初一晚上,小伙伴们就在这片地里开“春晚”——很简单,我负责“舞台设计”,也就是用铁锨挖出一块场地,还是有主舞台和次舞台还有通道的那种,地上堆满零食,翻出爷爷家所有蜡烛点燃插在雪地里,每个小伙伴准备一个节目,唱啊跳啊吃啊,然后在舞台中间放烟花,叫大人们一起来看。
越长大,过年也渐渐变得平淡,好像春节只是一个节,但对春节的期盼好像是我骨子里的一部分,我依然期盼一桌子的年夜饭,依然享受和家人们在一起,依然喜欢看春晚——但我不爱放炮了,不知是从哪年开始,突然就不爱放炮了,今年我家什么花炮也没买,爷爷家也没人从来成箱的花炮了。小时候放花炮,炮越大越兴奋,现在看那些大花炮简直就像看到个炸药包。我家大年初一有一个习俗,那就是全家人要按照辈分从小到大给爷爷奶奶磕头,磕九个头,然后再给二老说些话,爷爷奶奶就给红包,无论老小,都给,很有意思,像个节目。今年我磕完头对爷爷奶奶说,我已经长大了,你瞧,姐姐已经工作了,我是家里第二大的孩子,马上也要本科毕业了,自己也有这个能力分担家里的一些事情了,所以以后如果二老有什么需要做的,不一定只麻烦这些大人,也可以给我说。说完感觉即自豪又尴尬。每年等到所有人磕完头,爷爷都会乐哈哈地说明年我们大家会更好,到时候就给更多的钱。爷爷家现在住的房子是很老旧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搭建的平房,现在在我眼里是个危房,房顶还是槽型板搭的,以至于每次在青岛听闻乌市地震,都担心地先给这二老家里打去看看有没有事;房子还很小,用家里人话说,坐没坐的地方,站没站的地方,每次过年在爷爷家过,家里人多,聚在一起就更显得拥挤了,闹心,但温馨。爷爷是艺术家,他说他喜欢住在这里,过田园隐居的生活,但儿女们劝他买好点的房子,也能更好地照顾他们。爷爷看上了离我家和舅舅家很进的小二楼,一百多万的房子也是让他开始努力卖画。这年年夜饭饭桌上,尽快搬进新居是二老和我们的新年愿望。
看电视新闻,过年回家成了槽点。有逼婚的,有相亲的,有给压岁钱压力大的,有谈工作伤面子的……我一想,这不就是未来我要面对的吗。再过几年,春节对我来说就变成了一个七天长的假期,我不再是收红包说谢谢的,而变成了包红包说不客气祝你学习进步的;我不再是坐在桌前等大人们端上年夜饭的,而变成了在灶台前努力将锅里的菜翻炒成烹饪书上样式的;我不再是在电视机前等着看魔术穿帮的,而是伴随着鞭炮声给老板同事发拜年短信的……想到这里我叹了口气,如果我早知道年味在童年才富足,在什么都理所应当的年纪才珍贵,我想我会更加珍惜春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