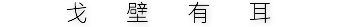my Instaqgram: http://www.instagram.com/zhanggeer
寒露
偶尔会从食堂的电视里,或是谁谁谁的嘴里得知,今天是夏至了,今天是芒种了,明天是春分了。前几天忘了是从谁的嘴里听到说,寒露到了。高二那年的寒露,气温骤降,大雨临盆,放学后,我和朋友在雨中战战兢兢招手搭出租车回家,边走边搭,结果都快走回家了,还是没搭到一辆,到家后打开电脑,边用毛巾擦干淋透了的头发,边在word打字,形容天气多么恐怖,车流多么冷漠,然后发了一份给晚报编辑。今年的寒露,秋困准时来袭,它伏在课桌下,趴在椅子上,藏在从自习室回宿舍路上的灌木丛里,不经意间就会扑出来,将我牢牢捆住,浑身无力,只想找张松软的床美美地睡一觉。
这几天呢,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平淡的生活里穿插着些不疼不痒的琐事。唯一的“大事儿”,就是在黄金周的最后一天,好友黄家鲁终于来到了青岛。
黄师傅和他父母一起回山东探亲,之后来青岛“专程看我”,然后再返校上课。他是7号早晨,从烟台乘大巴抵达青岛的,我下午才去找他。我们在阳光百货下汇合,我们热烈拥抱,他先夸赞了我变长的发型,我夸赞了他又变胖了一些……我和他的妈妈握了手,他妈妈对黄家鲁说,你看看人家多苗条,我说,唉,不行不行,男生这么瘦不好,不好。我们一起打车去中国海洋大学崂山校区,黄妈妈的好朋友的女儿在那里上学,特意去看看她,一起吃个饭。我觉得这场合还蛮奇怪的,不过还是蛮兴奋,好歹也是次社交活动,我已经很久没参加过这样的活动了。我们在海大附近很偏僻的一家农家乐吃了顿便饭,几道简单的菜,几句闲聊,一切简单,蛮开心,那女生看起来比较学霸,好在性格开朗,健谈,不装B。那女生在海大外院读书,德语专业,她也带了个朋友,那朋友读日语专业,我觉得还蛮亲切的,毕竟都是学外语的娃娃。吃过饭呢,我们就打车返回住宿的地方。黄家鲁一家人住在香港中路的全季酒店,位置好,环境好,价位好,我就在心里check了这家酒店,下次带朋友住这里好了。我和黄师傅住4楼,他爸妈住11楼,我们简单地收拾了一下,黄家鲁背上了单反,我们去夜游青岛。那晚哦,我们拍了好多照片。黄师傅对自己的照片要求超高,“哎呀双下巴出来了”,“靠!肚子咋照这么大”,屡次要求重拍。我们在晚九点的香港中路数山东美女,在十点以即将熄灭的海岸夜景当背景定时自拍,在午夜的奥帆中心向海里撒尿未遂,在马上打烊的Starbucks他问我该喝什么呢,我请了他超大杯美式咖啡,导致他在青岛待的唯一一晚,没有睡着。
第二天,黄家鲁很早就起来了,不停地催我赶紧起床——应该是,一宿没睡的他,一大早就不停地催我赶紧起床,不然在1点退房去机场前没法逛完那些我答应他要去逛的地方了。我呢,并没有作太多复杂的计划,老三样:栈桥,天主教堂,八大关。我们在4个小时里蜻蜓点水般地逛了青岛大部分景点,午餐是王姐烧烤,我和他一人要了一串肥大的鱿鱼和粗壮的鱿鱼腿,吃得又饱又累,因为我戴着牙套,吃起来实在不方便。在路上,我问他,青岛舒服还是南昌舒服,他说我靠你这不废话吗,我说,搬到青岛来?他说,好啊。虽然我不知道毕业后自己是不是留在青岛,但我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搬到这里来。黄师傅买了六张很好看的风格简约的明信片,背面是青岛著名景点的水粉画,在酒店退完房,他伏在大厅的写字台写完了这六张明信片,分别写给了犀利小队的六个人,除了地址,他只送给每个人五个字,这五个字根据收信人的特点,分别是:祝越来越壮,祝越来越瘦,祝越来越帅,祝越来越美等等。因为要赶飞机,没有时间找邮筒,他就把明信片交给了我帮他寄出去。我送他们一家去了机场,他爸妈飞回乌鲁木齐,他则飞回南昌开始大学的毕业季。我把他送进了安检处,道了别。在这个安检口,我送过包括爸妈在内的我爱的人,每次我都是目送他们消失在曲里拐弯的毛玻璃墙组成的安检口,匆忙地招完最后一次手,转身逆着人流离开这座机场。
出了机场,我在这座城市上演过的所有的离别的悲伤和相见的喜悦,逐幕闪现,身后是一架架离港的飞机穿破云霄。我多希望我坐在一架没有目的、永不降落的飞机上,飞机里装着我的家人和朋友,我们在对流层追着太阳,带的所有书籍已经看完,机上的饮料和餐食已经尝遍,我也已经和空姐聊得很熟络,飞机机尾贮藏大小便的装置已经快撑爆。飞机上没有寒露,我们怀着对幸福和未来的怀疑,等待降落。
落地后,先把黄家鲁的明信片寄了。
And when the broken hearted people living in the world agree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For though they may be parted, there is still a chancec that they will see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最怕的东西
我最怕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我还清楚的记得,4岁的时候,爸爸从幼儿园接我回家,路上,他谈起人的生老病死。他说,爸爸妈妈会老去,老去,然后会离开这个世界,我问,去哪儿?他说,去天上,那时候你就见不到爸爸妈妈了。无论是我爱的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是我幼儿园里欺负我的同学,无论是电视里的金龟子,还是楼下的维族叔叔,他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我吓得嚎啕大哭,大喊我不要爸爸妈妈走,我不要爸爸妈妈去天上,爸爸说,好,好,我们不去,我们哪儿都不去。
那次是我第一次知道“死亡”这个概念,我也终于知道,人是会死去的。
在从青岛流亭机场送完黄家鲁登机回学校的公车上,我突然想,我已经一年没有回家了。和家里常通电话,非常偶尔会视一下频,虽然在听筒和屏幕里难以发觉爸妈衰老的迹象,但我知道,有那么一天,他们也将变成被年轻人嫌弃步伐缓慢的老人,公车上被让座的“老弱病残孕”特殊乘客之一,两鬓斑白,老年斑从脸颊延至脖颈,手背松弛的皮肤包不住青色的血管,浑浊的眼睛,只能认清自己的儿子——我。天哪,想到这里,眼泪没忍住。
从小就有人说,美国的孩子18岁就独立了,他们离开父母,独自生活,很久很久才回家探望父母一次。他们的家庭观念到底怎样,我不曾考究。我想,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像我一样吧,每每想到父母总有一天会去天上时,就会难受得要死。我不知道我这样算是懦弱,还是太顾家,还是怎样。我已经快一年没回家了,我很害怕这次寒假回家时,看到爸妈的衰老迹象。
我知道,我也会变成这样,可我能够从容接受自己的衰老和死亡。但我接受不了爸妈的衰老,不想让他们去天上。我想,这就是我最怕的东西了。
我们哪儿也不去。
(2013年大年初一,摄于乌鲁木齐市体育公园。这是家庭的一项传统,每年的大年初一,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这间公园的这个长椅——拍摄一组照片,以记录岁月变迁,已经记录近10个年头了。)
趁发型没乱
我告诉了理发师
想留个combover复古发型
他说我头发还太硬太短
但会在我离开青岛前
让我的头发变成想要的样子
剪完头
吹啊吹啊
吹完头
打了两遍发蜡一遍发胶
像做泥陶
头发终于算是听话 被梳向了后头
但还是倔强 总有几根立起来
我去买了个发箍 将他们扣起来
听话了许多 帅气了许多
朋友在镜子里笑啊
说好丑
朋友在镜子里闹啊
说这是考研头吗
这是一颗始料未及的combover头
想像一首歌里唱的 我如自己的头发般自由
趁这发胶发箍还在头上 趁这发型没乱
纪念4s君
非常遗憾,伴我一年半的手机,同死神在病榻上搏斗了七天,最终医治无效,于今日下午在苹果官方售后维修点宣布死亡。
2012年的小年夜,母亲花了5200元,把这部iPhone4s领回了家。我是苹果迷,这是我的首台iPhone,初次见面当然爱不释手,从此便和他形影不离。他改变了我的生活。他肚里有那么多iTunes Plus AAC洗脑歌曲,有那么多好玩的限免游戏或从淘宝买兑换码换来的app和游戏,供我娱乐。他有各式各样好玩的相片处理软件,瞧我的头像,就是他给我做的。他有一副清晰的摄像头,且看我做那么多鬼脸,甚至裸照,还能忍住不笑或不被吓cry。他有很多社交软件,让我认识了许多朋友。他帮我完成了许多梦想,比如,我的“戈耳卫视”的所有原创视频,都是他来拍摄并后期制作的;他是我的助理,催我起床,提醒我那些事情还没做;他像是邓布利多的冥想盆,他的备忘录里记录着我所有的突发奇想。他的通讯录里,替我存着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人。他让我和家人、朋友保持通讯,电话,或视频,青岛,到乌鲁木齐。
他是一台手机,摸上去冷冰冰,但他甚至比某些人有人情味。
可就在七天前,他突然昏迷,再也无法开机,连接电脑或充电器进行心脏起搏术,也没能救活。我抱着他辗转各大维修店,没有人能治得了他,甚至开膛破肚,都找不出病因。今天中午,我再次启程送他医治,大夫连接了电脑,尝试刷机,他的屏幕竟然亮了!苹果标志。可大夫却拔下数据线,告诉我,没法修好了,全青岛都不会有人修好的,建议我苹果官方售后看看。我来到位于台东的青岛官方售后,因为这两天让私人拆过机,无法再返厂换机,医师最终坚定,脑死亡,且没有救活的可能。
伤心啊,亮着的屏幕,苹果的logo,像还在呼吸,心脏还在跳动,但再也不能说话了。
我按灭了屏幕。
他走了,现在他就躺在我的手心。他的离开是为了我专心追逐理想。没了他,我当然能正常地过活,但我会很想念他,也许,他有太多和我在一起的使用心得,去天堂,分享给乔布斯——毕竟,他是乔布斯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