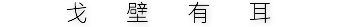奶奶已经住了近十天医院了。从元旦开始,她上吐下泻,打了针吃了药,情况不见好转,只得住院,住院后诊断为急性肠胃炎。我元月8号中午从青岛抵乌鲁木齐,下午便去医院看望她。见到我,她有气无力地说“我的孙儿来了”。
奶奶蜷缩在床上,有些皮包骨,鼻子吸着氧。为了装上假牙,把原有的好牙全部拔掉了,同半年前见到的她不同,她的嘴是凹陷进去的,就是电视上老年人牙齿掉光后特有的那种凹陷。病床边吊着的一大袋乳白色的营养液正在输进她的身体,床边还放着一个专用的尿盆,想方便的话在床上就可以解决。病房里就这一张床,几只沙发,平日看护的家人就在那张长沙发上休息。这天她的情况不错,吃了点小米粥。可是第二天,她又无法进食了,吃多少吐多少,喝水也吐。这晚我陪护,帮她换尿盆,喂水,按摩腿脚。早晨医生来查房,询问奶奶的情况,奶奶说肚子不舒服,医生就在她腹部这儿敲敲,那儿捏捏,完后医生把我叫出病房,说奶奶无法进食、上吐下泻的情况可以确定下来是胆结石导致的,刚住院时查出有胆结石,但现在看来,结石情况愈发严重,并伴随有胆囊炎。后来的检查发现,结石已经堵住胆囊,还化了脓,必需要做手术了。
手术并不危险,保胆取石、吸脓是小手术,不需开膛破肚,用腹腔镜即可完成。但是对于奶奶来说,真正危险的是这次手术的麻醉。由于奶奶一直有溶血性贫血,血液一些指标较常人来说低一些,若麻醉使用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因此,家里托关系找来了院长,由副院长主刀,还请来了全国最好的五位麻醉师之一,望降低所有可能的风险。
手术当天,儿女到齐。我在想,这么多人在这里,会不会让奶奶更加紧张?十二点,从血液中心调来的血液已经输入奶奶体内,两点多,奶奶从内科住院部转到了外科楼18楼,推进了手术室。这是我第一次来手术室——的外面。18楼只有一条不长的过道,一边是一排座椅,过道尽头就是手术室的大门,上面写着“家属免进”。旁边有一个安装了栅栏的玻璃窗,上面写着“亲属沟通窗”,手术室内有任何情况,医生将从这个窗户和家属沟通。
爷爷奶奶信佛。爷爷特地吩咐小舅在奶奶手术时抱着佛像,愿佛保佑。奶奶住院时,这个佛像就摆在病床边的书柜上。
一个多小时后,一位穿着深绿色手术服的医生拉开“家属沟通窗”,告诉我们手术顺利,各项指标都正常,可以顺利完成。我小声说了句“YES!”一会儿又有一位医生,透过窗口给我们看从奶奶胆囊里取出的“石头”,暗褐色的小碎石在铁盘里摆了好长一溜,还给我们看了抽出的化脓的胆汁。健康的胆汁是墨绿色,奶奶的胆汁已成暗黑色。看来,手术真的很顺利,我竟高兴得不自觉鼓起掌来。紧张的大人们也都松了一口气。
术后,奶奶直接转入ICU重症监护室,观察一天。
嗯,一切顺利。希望她尽快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