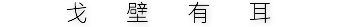昨晚第一次在我租住的地方和老妈视频。“我租住的地方”,讲起来是有些别扭,我就是矫情地觉得这地儿还不足以叫“家”,我也没法顺其自然地说“我每天几点回家”或者“我到家了”这样的话,因为我只在这儿租住四个多月啊,满打满算五个月,初试一考完,我就回家了,会真正的家,离开青岛,可能不会再来了。我也只是晚上和中午在这儿睡个觉,洗澡洗衣,偶尔在这儿吃个饭,所以这里充其量是个宿舍吧。
这里也可以叫“陋居”。1300块一个月的高层住宅也没资格当陋居,可昨晚视频时,我给我妈展示完我的房间后,她就觉得这里是陋居了。你看,我的房间的确很小,床也小,没有衣橱。我用的是上个租客留下的建议的布制衣物收纳橱,刚搬来那天我闻见这橱子散发着浓烈的狐臭味,就拆了支架,把外面那层布扔进洗衣机里搅了搅,后来发现那狐臭味就是这布料本身的味道。我的房间是没有窗帘的,白天房间透亮,像同开五盏日光灯,午睡就比较困难了;晚上房间就太通透,对面那栋楼密密麻麻的灯火让我紧张,万一有个偷窥狂隔楼观我怎么办。因此在搬来的第一周,我就去附近的市场买了一块床单当作窗帘,宜家风,25块。窗户没有窗帘杆,只有左右各一枚钉子,我就用晾衣夹夹住床单两边,刚好可以挂在两边的钉子上。早晨起床,伸手用力一拽,窗帘就“哗”地铺天盖地了,也是方便,但挂上去就比较麻烦,每次都需要爬上爬下。
只要有我在的地方,我能填满一切空档。我这不大的房间已经被我搞的满满当当。没有床头柜,我就用行李箱当床头柜;没有挂衣架,我就支起相机三脚架当挂衣架;没有书架,我就索性在墙根上把书列起来。我欣然接受这样的简朴,也享受这样的简朴,因为我终归要搬走,留下并带着胜利的喜悦。